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2021年年末最后一個大瓜“花落”張庭和她的品牌“TST庭秘密”。石家莊市裕華區市場監管局披露了“TST庭秘密”運營主體公司上海達爾威涉嫌利用網絡,從事傳銷活動被查處的進展。據了解,達爾威此次被財產保全凍結的資金有6億元。對此,“TST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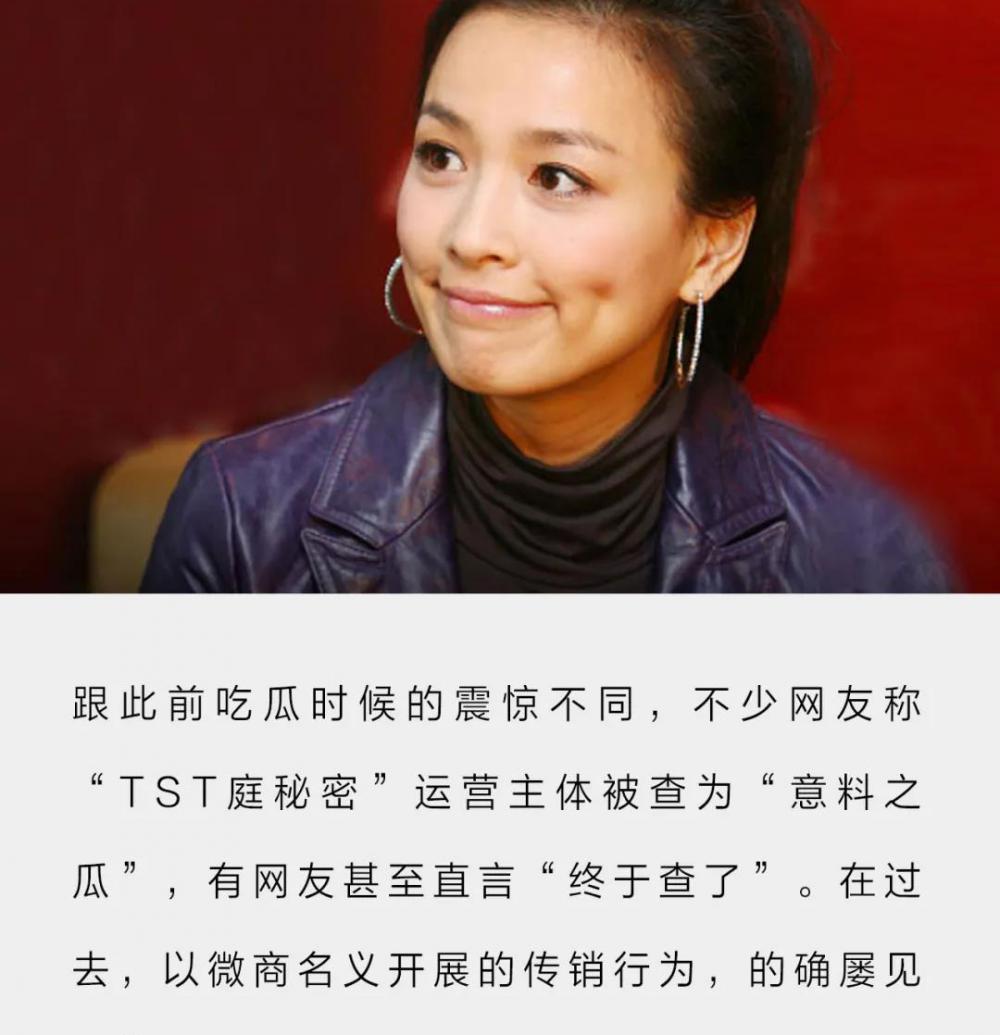
2021年年末最后一個大瓜“花落”張庭和她的品牌“TST庭秘密”。
石家莊市裕華區市場監管局披露了“TST庭秘密”運營主體公司上海達爾威涉嫌利用網絡,從事傳銷活動被查處的進展。據了解,達爾威此次被財產保全凍結的資金有6億元。
對此,“TST庭秘密”在12月29日凌晨回應“達爾威是合法經營的公司”,公司負責人演員張庭、林瑞陽夫婦則通過轉發微博的形式力挺。
但事實是,市場監管部門回應媒體時稱,相關傳銷組織從2013年開始,涉案人員多、金額巨大,已進入到財務審計階段。有關案件性質、責任認定靜等調查結果。《人民日報》的態度則是“剜掉網絡傳銷毒瘤”。
有意思的是,跟此前吃瓜時候的震驚不同,不少網友稱此事件為“意料之瓜”,有網友甚至直言“終于查了”,言語間頗有種宿命感。在過去,以微商名義開展的傳銷行為,的確屢見不鮮。
01、賺翻了
2016年,趙洋在同學的介紹下做了“TST庭秘密”的代理。
吸引她加入的原因有三點:一是賺錢多;二是操作簡單;三是張庭等一眾明星的站臺。“同學跟我說誰誰誰做了這個,一年能掙十幾萬、二十幾萬,我自己一個月才掙4000塊錢,明明咱還比他們多上幾年學,為啥咱不行呢?”
這名同學還告訴趙洋,只需要在朋友圈分享產品鏈接就能賺錢。剛做的時候,確實有人通過朋友圈來找趙洋買貨,她把這個消息告訴那名同學后,對方慫恿她還能賺更多的錢。
辦卡、自己創辦公司,讓更多人開卡,一起沖業績,是在“TST庭秘密”賺錢的“奧秘”。“只有自己辦公司、做董事長,裂變出來的子子孫孫(下線)才跟你有關系,他們買貨的時候,你才能拿到提成。”趙洋說。
(受訪者供圖)
她加入TST的時候,能自己創辦公司的前提是,發展100個人“開卡”,自己和直系代理的業績連續三個月每月達到10萬元。
為了沖業績,趙洋沒少囤貨。她本以為當上“董事長”后就賺錢了,令她沒想到的是,自己囤的貨很難賣出去。
原因是,市場上的代理商都在打折銷售,想要賣出去只能跟著低價銷售。而TST的代理商是拿貨越多,折扣越低,想要在賣的時候有價格優勢,只能多從TST拿貨。
為了鼓勵像趙洋這樣的代理商,TST還會許諾,業績好的代理商可以和張庭夫婦合影、加微信。“后來我才知道,微信是加了,但微信后面根本不是他們本人,是助理。”趙洋說道。
(張庭、林瑞陽)
趙洋做了四年TST代理,可到頭來發現自己根本掙不到錢。跟她“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同,張庭夫婦卻靠著TST賺得盆滿缽滿。
TST成立于2013年,創始人為林瑞陽、張庭夫婦。官方APP顯示,其主營產品有TST護膚品、大健康產品、進口紅酒等。目前,TST擁有近1300萬會員,覆蓋消費者超過1億人,TST創始人公司達3368家。
TST的運營主體公司為上海達爾威貿易有限公司,天眼查APP數據顯示,張淑琴(張庭本名)為上海廣鵬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勝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的老公林瑞陽(原名林吉榮)是上海達爾威最終受益人。演員陶虹,共計持有上海達爾威6.6%股權。
這個公司有多賺錢呢?趙洋向市界舉了一個例子:TST品牌一款“黃金備長碳”面膜零售價約30元/片,同款面膜,其代工廠在阿里巴巴的報價為4元/片。
上市公司山東華鵬之前曾公布過一組數據:2017年1—9月份,上海達爾威貿易有限公司營收達36億元,凈利潤達11.4億元,凈利率為31.7%。
和同行企業對比看,2017年丸美股份、珀萊雅、上海家化甚至華熙生物的凈利率都遠遠比不上上海達爾威。比如,華熙生物生產的玻尿酸,素有“女人的茅臺”之稱,但2017年其凈利率比上海達爾威低4.5個百分點。
納稅額也能看出上海達爾威的實力。據上觀新聞報道,2018年上海達爾威納稅額達到12.6億元,是上海市青浦區的納稅冠軍,將同區域的中通、申通、韻達三家公司甩在身后。
坐擁這么賺錢的生意,張庭夫婦也“壕氣”十足,他們在上海的豪宅毗鄰黃浦江,不僅面積大還帶有空中花園。張庭曾在節目中說:“第一次來我家的人都會迷路。”
02、涉嫌傳銷的生意經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TST的生意經和2019年爆雷的傳銷公司權健等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權健創始人束昱輝曾開著直升機回鄉探親、高價冠名足球隊,處處彰顯自己的財力。TST不僅靠眾多明星站臺“撐場子”,還一直對外宣傳多少人靠TST代理“一夜暴富”。
(張庭、明道、陶虹)
其實,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都是為了包裝自己,吸引更多的人加入。“TST就是把原來權健們在線下的模式搬到了線上而已。”“李旭反傳銷詐騙團隊”負責人李旭告訴市界。
事實上,早在這次被舉報前,TST就被多次懷疑涉嫌傳銷,卻都予以否認。“TST庭秘密”負責人曾對媒體表示,“庭秘密是B2B2C模式”。
具體來說就是,公司一方面是直接把產品賣給消費者,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代理商來銷售,并強調“代理的所有收益都是以產品銷售獲得,所有模式均不存在拉人頭獲取收益,更沒有涉嫌傳銷”。
官方平臺上,TST把自己定義為微商。一定程度上,微商和傳銷模式,似乎很容易被混淆一談。
李旭認為傳銷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入門費”,即需要繳納一定的費用,或者以購買產品的形式交錢加入;二是“拉人頭”,形成明顯的上下線關系;三是“團隊計酬”,即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形式通過拉人頭的數量或業績給予一定的獎勵。
“如果沒有多層次的激勵機制,就沒人去玩這個東西了,說白了都是想賺錢。”李旭補充道。在他看來,TST的經營模式幾乎和傳銷的特征一模一樣。
資深反傳銷人士、志愿者王庚新認為,上海達爾威貿易有限公司依托價格虛高的產品系列,采取團隊計酬模式,披著微商的外殼,本質上就是典型的傳銷行為。
李旭表示,區分真正的微商、社交電商和傳銷,主要看兩點:一是是不是三無產品,產品有沒有性價比;二是有沒有多層次返利,“層層拔毛”。
“紅酒、茶葉、化妝品這類生產成本低的產品最容易被傳銷公司利用。高額的利潤才能支撐起層層分利。而且參與者的收入并非產品利潤,而是發展下線的人頭費。”王庚新補充道。
03、微商早過了草莽階段
若沒有傳銷抹黑,微商其實也有過一段傳奇經歷。
起初,有微博“大V”利用自己的人氣在粉絲中間開展商業營銷,獲得了不少利益。這番操作也給不少人提供了賺錢新思路,有人開始在微博、人人網、論壇、QQ等展示和推廣產品。這便是微商的雛形。
變局發生在2011年,微信上線,打出了“連接一切”的口號。人們發現在微信不僅可以發表產品的圖文介紹,還能迅速溝通,并且推廣除了打字費點時間外,沒什么其他推廣成本。于是,微商營銷的主戰場很快轉移至微信。
最先嗅到商機的,是一群做海外代購的人群。他們把代購來的商品照片發到朋友圈,吸引了不少人留言咨詢。這個時期微商賣的產品多為以箱包為代表的奢侈品,以奶粉、紙尿褲為代表的母嬰用品以及一些化妝品和電子產品等。
(微商代購裝滿行李箱)
尤其是在2013年,微信公眾平臺升級成訂閱號和服務號兩種類型,疊加微信支付誕生,社交屬性和商業營銷屬性兼備,在這樣的背景下,微商開始野蠻生長。
這時期,微商有兩種賣貨方式,一個是通過微信公眾號弄一個入口,另一類則還是把朋友圈當成主陣地,尤其是工資較低的打工者、在校大學生和全職媽媽,是第一批從業者。
不少人對那一年的微信朋友圈印象頗深,王麗用“大雜燴”來形容她的微信和朋友圈,有時候她會被朋友群發廣告,有時候去線下會被店主熱情地要微信,轉頭就能看到店主在朋友圈賣貨,有時候她還會被一些禮品誘惑,加入到一些產品推廣的群聊里。
“最魔幻的就是,可能上一秒這個人還在別人的朋友圈底下留言買東西,下一秒就開始自己發朋友圈賣貨了。”王麗形容微商“簡單、粗暴、直接”。
微商被真正引爆是在2014年。那一年,不少微商開始相信“年營收10億不是夢”,靠的就是面膜這個單品。比如面膜品牌俏十歲,憑借微商銷售額直接過億,微商發展到兩三百萬人。
就連俏十歲的創始人武斌都沒想到能爆發成這樣。受財富的誘惑,微商規模迅速放大,各種層級代理模式頻出。到2014年底,微商從業者已達數千萬人。
大量微商品牌隨之涌現,有的依托代工廠的貨,貼上自己的牌子,還有傳統品牌入局微商領域,把銷售渠道從線下轉到微商。韓束、思埠、三草兩木、凱兒得樂等品牌均屬于此列。
不少明星加入其中,除張庭外,“美麗教主”伊能靜創立了面膜微商品牌“膜法伊人”;劉嘉玲創立了“嘉玲面膜”;就連郭德綱也賣過微商面膜。
一邊是明星站臺、草根財富故事的渲染,另一邊卻是亂象滿天飛。
由于個體賣家魚龍混雜,真假貨品難分,以次充好,價格不透明,同時有些品牌還有質量問題,比如用了面膜之后爛臉,甚至有些微商為了賺快錢,利欲熏心,轉變成了傳銷獲不義之財。
微商成了負面的代名詞。2015年之后,微商漸漸地從原先的“我們是朋友所以我相信你”變成了“做了微商從此朋友是路人”。受此影響,2015年5月起,多數微商企業銷售額下跌了80%-90%。
同時,各方面對于微商的監管也開始加速。2015年,工商總局首次明確提出將微商納入監管;微信官方對微商的政策也從鼓勵轉變為嚴肅監管,從“打假活動”、限制暴力刷屏到后來限制每天加好友人數、關停三級分銷微商城、關閉微信營銷號等等;2017年,微商法律規范征求意見稿公布。
微商逐漸從野蠻生長步入規范發展階段,與此同時,阿里巴巴、網易考拉、京東等傳統電商企業紛紛涉足微商,不少大品牌也介入該領域,使得一些產品被迫出走,有的還轉戰到小紅書、抖音等其他平臺。
另外隨著消費升級,用戶也開始轉變,對于“三無產品”十分警惕,錢也不再那么好賺。
靠微商起家的不少人也不再高調炫富,反而開始大倒苦水。比如微商教父龔文祥從前被媒體報道都是“又發了多少萬的紅包”,最近一次卻是因為“負債累累,賣房賣車,傾家蕩產,身無分文”。
魚龍混雜的微商經歷一波洗牌,開始往正規軍方向走。從前的微商如果順著潮流,一心一意謀質量,打造優秀品牌,自然也是一條出路。
只可惜,有些人不愿放棄到手的利益,忍不住動了歪心思,從微商變成了傳銷,掛羊頭賣狗肉,這種打擦邊球的行為,終被啄了眼。
(趙洋、王麗為化名)
參考資料
《論微商的發展歷程及未來方向》,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
(除單獨標注來源外,以上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作者|齊敏倩 華宇 編輯|劉肖迎)

王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