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從12歲開始決意離鄉,到40歲以后無法還鄉,和家鄉與親人的距離,只有幻想才能彌補。?主筆|王珊記者|印柏同編輯|陳曉一本科幻底稿北京皮村和四年前不一樣了。自2017年以來,這座位于飛機入港航線下面的村莊有了很大變化,做了硬化水泥路,村里不再
從12歲開始決意離鄉,到40歲以后無法還鄉,和家鄉與親人的距離,只有幻想才能彌補。
?主筆|王珊
記者|印柏同
編輯|陳曉
一本科幻底稿
北京皮村和四年前不一樣了。自2017年以來,這座位于飛機入港航線下面的村莊有了很大變化,做了硬化水泥路,村里不再塵土飛揚;露天旱廁拆除改建成沖水廁所,有專門的人打掃衛生。村里兩三層的樓房大多被四層公寓替代,因為租金便宜,越來越多的白領來這里租房,皮村不再只是農民工聚集的地方。沒有改變的是,天上依然有飛機以兩分鐘一架的頻率飛過,引擎聲轟隆著滾過村莊上空。如果閉上眼睛,會以為自己身處戰爭時期的防空洞。
但范雨素的生活沒什么變化,她仍然住在這里,租一間加蓋在二層樓上的屋子,層高很低,看著只有一米七左右。房間里沒有熱水器,沒有燃氣,做飯要在走廊支電磁爐,房租一個月500元——這不是想象中一位“名人”的生活。
范雨素是在四年前成名的。那時她還是一名在北京打工的湖北農婦,帶著兩個女兒,以做育兒嫂為生,閑暇時喜歡看書寫作。她的一篇自述性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網絡上走紅。文章用的是那會兒比較流行的非虛構體,記述了她出生的村莊、家庭,以及自己離鄉后在城市漂泊的經歷,文字樸素又不乏幽默戲謔。文章發表后,閱讀量達到400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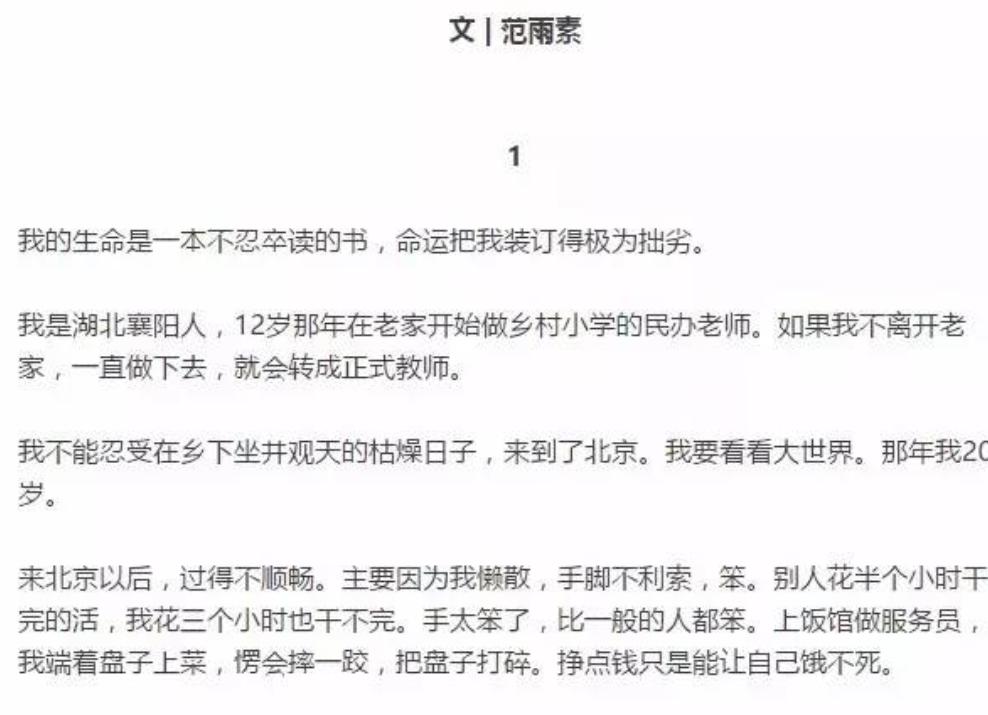
《我是范雨素》文章截圖
《我是范雨素》在網絡上發表那天,范雨素抓著手機盯著閱讀量,在窄小的房間內來回踱步。手機是大女兒10年前淘汰給她的,粉粉嫩嫩的顏色,屏幕上端碎裂成蛛網狀,卡頓時“跟得了偏癱一樣”,連微信支付都用不了,但能看到文章的閱讀量噌噌往上漲,“發火箭似的”。她覺得自己一天之內掉進了輿論的旋渦,第一批來找她的媒體就超過30家,她走哪里,記者跟到哪里,浩浩蕩蕩的,讓她講寫作的初心和經過;手機里短信提示音響個不停,又卡了。
出名給她帶來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機會。因為當過育兒嫂,有一個媒體平臺邀請她寫育兒,每個月出四篇稿子,每篇1500字,一個月就有上萬元收入,她沒接。也有不少電視臺找她去做講座,她不去,“推掉的出場費加起來都有3萬塊了”。最有吸引力的是一家出版社拿著20萬元現金,要簽她的作品,她連面都沒見。
范雨素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她覺得這座城市有文化(者也 攝)
范雨素有自己的打算,她說不想寫那些輕飄飄的東西。所有對《我是范雨素》的評價中,她最喜歡的是“有力量”,她打算用更大篇幅繼續“有力量”的書寫。為了有時間寫作,范雨素辭了賴以為生的育兒嫂工作,僅靠每月打零工的兩三千元收入維持基本開銷。寫作過程比想象的困難,她總是下不了筆,不知道如何開頭和敘述。實在沒有辦法,就給自己做硬性規定:“每天寫夠十頁,跟干體力活兒一樣。”有時候沒有靈感,她就喝點酒,趁著酒勁兒寫;實在寫不出來,就將字寫大一些,湊夠十頁,“就像掃地,你每天必須干夠這些量”。
讓人驚訝的是,她最終交出的底稿是一本“科幻小說”。小說里,范雨素和家人們帶著各自顯赫的前世,生活在一個叫打伙村的村莊。他們之間所有的行為、關系,包括承受的苦難,彼此的疏離、怨念、恨和愛,都是冥冥中的前世通過一些玄妙的物理學理論在起作用。
這跟編輯最初的想象不太一樣。《我是范雨素》文字和視角給人最大的感受是真實,是普通人觀察生活的視角。語言沒有經過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處理,文字沒有表演性,甚至看不出她有很明確的寫作意圖,這件事本身就很打動人。可是范雨素交出來的這部底稿,題材和風格都跟《我是范雨素》不太一樣。雙方對文本的理解有些偏差,幾次溝通并不是非常順暢,最后沒能在合同約定的時間如期出版。
但范雨素說,這部“科幻”底稿是她“成名”后的第一個完整作品。如果《紅樓夢》和《西游記》打9分,她給自己的作品打7分。書中是一個幻想的世界,但又包含了她所有的經歷。寫作時,范雨素覺得自己像個創世者,可以無所不能地構建,“就像開發游戲的程序員,是這個游戲世界的上帝,可以安排每一個人的命運。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是相通的。這種自信能夠轉換給現實世界中的我,讓我的自信增加,變得更有力量”。或許,這種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寫作,是她面對自己過去的一種方式。因為,那些日子“太苦了”。
小時候
范雨素出生在湖北襄陽市郊的農村,村子距離襄陽東站只有10公里,開車大約20分鐘。作為湖北的第二大城市,襄陽每年的外出務工人口在整個湖北省位居第一,這些人中有很大比例就是從襄陽東站出發的。它是中南地區非省會城市中的第一大站,往南抵達武漢,往北能到西安,往西則至重慶,往東至鄭州,到北京只需要四個多小時。
2018年,范雨素回過一次老家。那時高鐵還沒開通,她傍晚從北京西站出發,坐的還是綠皮火車的硬座,一晚上搖搖晃晃十多個小時,到家時天剛亮。離鄉多年,村子跟她記憶中的很不一樣:以前家家都是一層瓦房,現在卻是一溜的三層小樓,獨門獨院,干凈又闊氣。因為高鐵的修建,村里還有了酒店,入住的主要是技術人員和工人。“我媽老了,舅舅老了,嫂子老了。”唯一沒變的是家門口的三畝大池塘,水面還像小時候一樣開闊。
范雨素家有五個孩子,她是老小,上面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兩個哥哥要讀書、考大學,兩個姐姐一個發燒燒壞了腦子,一個有小兒麻痹癥。母親原來是村里的婦女主任,除了村干部的活兒外,還要照顧生病的兩個女兒,借錢給她們看病。范雨素說,大哥高考失敗后一心想當作家,買各種各樣的書,折騰出去不少家里的錢。大多數時候家里只能吃紅薯,偶爾能吃上一回饅頭。在范雨素的印象里,母親很能干,但一直是一張愁苦的臉,經常在家里哭。
父親不愛說話,年輕時在廈門當兵,還上過一年軍校,會修飛機。他跟母親是娃娃親,本來有提干的機會,母親怕他變心,堅決讓他退伍回了家。父親回家后整天黑著臉,寡言少語,偶爾才提起他在外面的見識。他會講廈門的炮聲,說那里一天到晚都在發射炮彈,震得人耳朵都要聾了;講北京軍區有哪個司令跟他是同一年入伍的,一起參加培訓,還提到有個大學教授是他的高中同學。雖然都是三言兩語的概述,但話里話外流露出一些意思:只要他愿意,找同學幫個忙,家里的生活就能改善。小時候,范雨素常盯著父親在天安門前的留影看,年輕的父親英姿颯爽,范雨素心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印象:父親是有能力讓家里人過上好日子的,只是他不愿意。“我那時就開始恨他,恨他不會賺錢。”他就像一棵大樹的影子,看得見,但沒有用。那會兒她讀到《傅雷家書》,便羨慕傅聰有一位能談藝術的父親,從戲曲、小說、美術到音樂,無所不能。“我要是也有傅雷這樣的父親,我可能也成為藝術家了。”
“我現在已經不怨我的父親了,經歷了苦難,我理解了。”2021年4月的北京,天氣漸暖,范雨素坐在我的對面,穿著一件紫色的毛衣開衫,圍巾也是紫色,是用心搭配過的。她個頭兒不高,一米五左右,梳著齊劉海兒,頭發蓬松、整潔地綰在腦后,看著比幾年前白一些。手指還是原來的樣子,因為做保潔,長期接觸水泡得有點發白,是一雙久經勞動的手。范雨素說,從小自己在家里就是個不被注意的人,“拿著一個小籃子,挎在胳膊上,和其他小孩一樣”,幫家里放牛、割草、割麥子。
只有看書的日子是快樂的。范雨素小時候愛讀書,沒有體系,遇到什么讀什么,有的是哥哥買的,有的是從親戚鄰居家借的。書里沒有父親的悶悶不樂和母親的悲苦,沒有生活的貧困,沒有對父親的怨恨。她喜歡看小說里故事發生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地圖上尋找對應的地點,看它在哪個大洲,如果是河流,又會流向哪里。她跟著書里的人物一起冒險、經歷村莊生活不會有的快樂和磨難。有一本書叫《梅臘月》,講的是解放初期云南少數民族的斗爭,里面很多人為了戰斗要溜繩索,攀爬懸崖峭壁,她就想象自己是其中的一員,跟著他們歷險,“溜繩索多勇敢啊,一個動作做不好就死了”。
法國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寫的《神秘島》,她印象最深。幾個主人公流落在荒島上,為了生存,不斷做各種實驗,制造陶器、玻璃、風磨、電報機,用手表的表盤借光生火,遇到困難還總有神秘人物相助。她在心里跟書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各個主人公都無所畏懼、勇往直前,仿佛世界上沒有他們辦不到的事情。他們影響了我,我成了他們,他們成了我,這給我帶來許多勇氣。”
12歲時,范雨素一個人離家了。起因是跟嫂子吵架,哥哥打了她,她一氣之下跑去火車站,學著書中知青逃票的經驗,跟著人流上了一輛開往柳州的火車。“恐懼”“害怕”,是那段經歷留在范雨素腦海中最深的印象。真實的外界跟她想象中太不一樣了,沒有處處拯救她于危難的神秘人物,維持三餐都很難做到。她去飯店打工,每天洗碗、洗菜、端盤子,手都生了凍瘡,還要被老板斥責“笨手笨腳”。晚上沒地方住,只能去車站睡。上世紀80年代的車站,聚集著各色各樣的人,流浪漢、搞傳銷的、拐賣兒童的……為了保護自己,她會找面相老實的人,挨著別人。“這樣壞人就認為我跟這人是一起的,不會來打擾我。”范雨素說,有一次她被一個民警叫醒,說有人在騷擾她。她揉著眼睛看了對方好久,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三個月后,她決定回家。“我年齡太小,一個人在外面無法維持生存,我受不了了。”
在村莊
30年后,在《我是范雨素》里,她這樣描述自己12歲時的流浪:“我按照知青小說教我的七十二道伎倆,逃票去了海南島。那里一年四季鮮花盛開。馬路上有木瓜樹、椰子樹。躺在樹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膩了,就到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說里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生活的。”
沒有苦難,沒有危險,更多的是詩意和浪漫——范雨素擅長這種表達方式。她寫自己在皮村的住所,把8平方米的小格子間稱為“總統府”:冬日陽光普照,還有兩條大狗的忠誠守護。有評論認為,這種“克制”的寫法,是她樂觀豁達的證明,也是她讓人贊嘆和尊敬的地方:不斷失敗,依舊陽光。或許這也是《我是范雨素》走紅的一個原因——她表達了一種讓人“喜聞樂見”的苦難,可以承受,可以消解,不讓觀看的人感覺沉重和負擔。
但對承受的個體來說,苦難并沒有這么容易跨越。它讓身體更粗糙,也讓心更敏感。四年前,出名的第二天,范雨素就躲了起來,拒絕接受媒體采訪。她給朋友發了條短信:“請轉告諸位,因媒體的圍攻,我的社交恐懼癥,已轉成抑郁癥了。現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廟里。我不能見任何人了。”其實,當時她就待在皮村的家里。成為眾人的焦點既讓她興奮,也讓她不自在。那些蜂擁而至的鏡頭,急切又莽撞,她懷疑它們的意圖。“把我拍得太丑了,像個妖怪。”范雨素說,“他們那么專業,肯定是故意的。”
人口眾多的皮村,對范雨素來說是一種保護色,誰都不認識誰,也就不會有人評價她(夏天 攝)
30歲以后,范雨素很少拍照片,“看到照片就像在回看自己的人生,不敢面對”。接受采訪時,她不喜歡講自己,總會將記者提出的每一個有關她的問題都扯到從書中看到的話,或者自己與名人的接觸。與她交談,像是在拼一個破碎的拼圖,費盡心力也難摸清她這些年的際遇。唯一確定的是,12歲時的流浪就像她人生的真正開端,此后她幾次離鄉,又幾次回去,在村莊和城市間來回游蕩,難以安定。
第一次出走又回家后,村莊已經不好待了。上世紀80年代,在農村的傳統觀念中,女生離家出走等同于私奔,“不好嫁了”。在村里人的指點和竊竊私語中,小哥哥幫她找了一份工作,在距離家八九里外的一所小學當民辦教師,教學前班和小學一年級,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家。很難想象一個只有12歲的小孩是如何管教幾十個孩子的,范雨素卻覺得不難,誰不聽話,就打手板,學生們因為怕挨打,學得都還不錯。她記得,有一次一個孩子因為沒寫作業挨了打,第二天,小孩哭著跟她說,手都腫了。
學校的日子如白開水一樣平淡,每天小學生放學后,她都去操場轉圈圈,因為“迷茫”“痛苦”。學校的早讀課,學生們讀課本,她在一旁讀《陶淵明集》,那位千年前帶著才華遠離城市,在鄉村過著窮苦生活的古人,多少給她一點安慰。從學校訂閱的報刊中,她還知道了許多哲學家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是“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第歐根尼。第歐根尼認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須滿足外,其他的都無足輕重。這是范雨素的另一種安慰:“你看他整天躺著不動,名氣還那么大,受每個人尊重。他就是偶像。”
范雨素說自己想跟人交流哲學,卻發現身邊沒有一個人能接住她的話題。隨著年歲漸長,相親、結婚被提上日程,同事和親戚一共給她介紹過三次對象。一個是郵政局的臨時工,范雨素覺得跟自己一樣不是正式編制,沒有同意;一個是大隊書記的兒子,談過很多女朋友,她認為對方品行不好;還有一個是村里的農民,她也沒看上。范雨素認可自己的價值,可心底又不免自卑。她總會提到一個類似天平的比喻:“民辦教師在當時地位非常低,連鴻毛都比不上。人家看你是什么人,就會給你介紹什么樣的人。”
她再次想到了離開。考大學在當時看來是唯一的方式,她報了成人自考,白天上課,晚上備考。為了逼自己進入學習狀態,她仿效古訓“頭懸梁,錐刺股”,在桌上放了一把亮晃晃的錐子,還不敢讓別人看到,“怕別人說這么用功還考不上,讓人笑話”。考試結果出來,數學和英語都很差,但語文過了及格線,考了60多分,“跟當年大學語文的錄取平均分差不多”。自己沒有上過高中,也能達到平均水平,范雨素說自己又有了自信,再次有了“赤腳走天涯”的勇氣。
去北京
1994年,20歲的范雨素辭去工作,獨自一人來到了北京。這是她第二次來北京,上一次是兩年前——參加成人自考后,到底是留在鄉村還是去城市,范雨素內心有太多困惑和迷茫。她覺得哲學家能幫自己,就一個人到北京,找到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位老師,她是從學校訂閱的報紙上知道他的。范雨素記得,自己是在臘月二十到的北京,那天刮大風、很冷,她只穿了一雙方口的布鞋,衣服也很單薄。見到那位老師時,對方很忙,態度卻很好。范雨素提出想在北大哲學系旁聽課程,老師問:“小姑娘,那你在北京能夠生活嗎?”范雨素一下答不上來了。
分別時,她往北大南門走,走了幾分鐘,感覺背后跟著一個人,回頭看,竟然是那位哲學老師。她意識到對方是在送她,心里突然一暖,“從小都沒人這樣尊重過我”。這段簡短的回憶使北京成為她離鄉后的首選目的地——這是一個有人情味、有文化的地方。她讀過的那么多書里,許多作者也都在北京,這讓她感覺親切,仿佛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里提前擁有了不少熟人,只要自己努力生活,機緣恰當,總有一天能遇見他們。
剛到北京時,范雨素在飯店打雜,端盤子、洗碗、拖地……早上4點多就要起床,晚上11點多才能躺下。偶爾空暇時,她會去瀏覽馬路邊的樓市廣告。那時北京房價才三四千元一平,50平方米的房子不到20萬元。她夢想能在北京買一套房,像一棵樹那樣成功移植到這個城市。
最初給她信心的是當時的丈夫,東北人,年紀跟她一樣大,是個包工頭。上世紀90年代正是北京大搞城市建設的時候,看著大工地一樣蓬勃發展的北京,范雨素覺得對方能干活兒,有潛力。她帶著他回了趟老家,母親和家里其他人沒說什么,只是看了一下對方的身份證,就同意了這樁婚事。可結婚后,對方不斷去發廊找小姐,賺的錢被揮霍干凈。范雨素想管,對方就打她,她越反抗對方打得越狠,有一次實在覺得痛苦,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被人救下來,昏迷了兩天兩夜。
圖|視覺中國
“家暴對她的影響很大。”范雨素的朋友王德志說,“最初認識時,她看任何人都是警惕的、小心翼翼的,只有熟了之后,才會稍微好一點。”《我是范雨素》火了之后,媒體涌進皮村尋找范雨素時,與她認識了三年的文學小組的成員,沒有一個人說得清她住哪里。很多采訪她都安排在女兒好朋友的家里,只有一個房間,10平方米左右,擺著簡單的幾樣家具。或者將人約在皮村的一個小飯店,聊天時伴著灶臺和排風扇的轟鳴,像極了天上飛機掠過的聲音。
范雨素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順利。她原名范菊人,因為出生在菊花盛開的時節,所以母親給她取了這個名字,寓意菊花開時成人形。但她十幾歲時看了瓊瑤小說《煙雨濛濛》后,給自己改名范雨素,象征雨中穿著白色連衣裙的美麗女孩。她曾向往的愛情也是瓊瑤小說式的:出現一個男人,永遠無條件地對女生好,不會介意身份地位的不對等。有一次讀到《平凡的世界》,書里的主人公孫少平靠寫書成名,擺脫了煤礦工人的身份,但沒有去尋找更好的婚姻對象,而是選擇照顧逝去師傅的妻子和孩子。范雨素讀了三遍小說,深深地被感動,感嘆自己身邊沒有這樣好的人。
她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也曾試圖再次相親,可婚戀市場對一個帶著孩子的農村婦女并不寬容,她受不了被人抬著眼睛從上到下打量。她帶著兩個女兒住到北京北三環的一處地下室里,將辣椒炒干、磨碎,然后加鹽,用來拌白水煮面條。那是回憶中“最黑暗的日子,覺得看不到光”。她在天橋擺攤,為了防止城管驅趕,出門一定帶著小女兒,以獲得同情。因為房租不斷上漲,她需要不斷搬家,“身份證一定要帶好,其他的都可有可無”。
她擺地攤賣過舊書,做過舊家具買賣,最穩定的一份工作是育兒嫂。出名之前,她已經做了10年育兒嫂。這個行當相對穩定,如果遇到合適的雇主,起碼能干上一年,這意味著一年都不用擔心收入。范雨素手腳不利索,做飯不好吃,但也有自己的優點。“有一次,有個雇主到家政公司,對著我們好幾個人問,誰會教杜曼閃卡(源自美國的一種嬰幼兒教育方法),他們都不會,只有我會。”
很少有一份工作像育兒嫂一樣,需要在兩個完全不同甚至帶著強烈差異的生活環境中來回切換。在雇主家里,范雨素常跟主人家的孩子一起住,往往是家里最好的房間,二三十平方米,有陽光,有空調,室內溫度一年四季保持26攝氏度。她跟過最闊綽的雇主,家里有1000多平方米,12個衛生間,有專門的阿姨負責打掃衛生,角角落落都擦得锃亮。還有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雇主,2000年初就背著一個價值七八萬元的包,相當于將“縣城的一套房子背在身上”。而范雨素在皮村的家,三個書柜全是從舊貨市場淘來的,加上一把椅子、一張桌子,才花了300塊錢,這是她來北京后給自己買的僅有的家具。“有錢人家的花錢方式跟我的花錢方式,那是兩個世界。”
皮村是一個打工者匯集的村子,本地人口不到2000人,外來人口卻有5萬左右(夏天 攝)
范雨素說自己在以旁觀者的視角看待“人世間的繁華和苦難”,“有時候也是麻木的”。有一年春節過后,她在家政公司等工作,來找活兒的人特別多,“把家政公司都擠爆了”。有一個農村來的婦女開始哭,說自己不識字,只會寫名字,沒有人愿意雇她。“她哭著訴說自己的經歷,有兩個孩子,丈夫還家暴她,但沒有一個人勸她。大家都麻木了,我也是。”
也有被刺痛的時候。有一次,一位熟悉的雇主約她出去吃飯,兩人都帶著孩子,點菜的時候,自己的小女兒將菜單搶了過去,指名要點紅燒肉,她“心里難過得要死”。還有一次,她跟著一位雇主去親戚家,吃飯時,雇主的親戚給她拿了一雙一次性筷子。每到這些時候,范雨素就提醒自己只是在做角色扮演,“我飾演的是一名育兒嫂”。
和童年一樣,只有閱讀能夠暫時紓解她的心情。狹窄的出租屋里,三個書柜里都是書,從廢品站和潘家園市場淘來的舊書,一塊五到三塊錢一斤。她還買了“微信讀書”的會員,每個月19元,可以下載幾百本書。她帶著兩個女兒一起讀。有段時間她們一起讀《佐賀的超級阿嬤》,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小主人公德永昭廣被母親寄養在佐賀鄉下的外婆家。雖然日子窮到不行,但樂天知命的外婆總有層出不窮的生活絕招,日子也就開心了起來。如果說童年的閱讀為她打開了通往外面的窗口,如今的閱讀則是她抵抗外界的一種工具。“我看文學就是要找到共情,找到共鳴。我現在讀文學作品都是在書中找自己,找不到就不看了。”
今年她最喜歡看的書是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書里,女主人公破譯了外星人的語言,有了看到未來的本領,在知道自己一生將面臨苦難之后,她依然選擇面對,按照自己向往的人生道路前進。范雨素對這個故事有了共情:“人家知道人生這么苦還勇敢面對,我的一生也得這樣。”還有一本官場小說,她也讀得流眼淚。文中的主人公是1979年從農村參加高考的大學生,碩士畢業后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最初他總是強調清高、面子,所以一直過得不好。在洞察人情世故之后,他變得實際起來,隨后一路官運亨通,生活也好了起來。范雨素覺得對方跟自己很像,都是為生存放棄了尊嚴。
寫作者
《我是范雨素》發表后,范雨素躲開前來采訪的媒體,卻看了每條評論,“得有1萬條”。有人將日本學者的評論轉給她,她看不懂日文,但也高興自己寫的文字傳到了國外。四年后,她還記得那些評論:“他們說我里面的每一句話都有歷史背景。比如我媽當選村干部,是建立在男女平等之后的;我出門打工,大的背景是中國的人口流動。還有人說我寫的文章把性別和階層交織在一起……”
不過,寫文章那會兒,她可沒想這么多。寫《我是范雨素》的緣起不過是有一天,80多歲的母親打電話跟她抱怨,說村里征地建高鐵,每畝地只給2.2萬元的補貼,村里人不同意,每家派個代表去談判。因為大哥出門打工了,母親一個人跟著隊伍,結果起了沖突,推搡中母親的胳膊被拉脫臼了。范雨素聽著揪心,覺得母親一生都過得太苦,越想越難受,就在紙上寫母親,寫了五個小時,寫成一篇《農民母親》。她將稿子給一位認識的編輯看,編輯讓她加點自己的故事,于是有了《我是范雨素》。
在網絡上成名前,范雨素寫作的時間并不長。她沒有受過專業的寫作訓練,除了閱讀,就是在皮村的文學小組聽課。這還是她來北京后的事。在這個偌大的城市里,散落著很多像她一樣,被某種懵懂但強烈的欲望驅使著,離鄉背井,帶著低微但驕傲的靈魂,在城市與鄉村間流浪的異鄉人。他們大多家境不好,穿著舉止也有些土氣,吃過很多苦,卻從未放棄從苦海中上岸的愿望。文學是他們救贖自己的一種方式,皮村則是他們的一個聚集地。村里有個文學小組,由一幫志愿者發起,每周會請北京各大高校的中文系老師來授課,教小組的成員們如何寫作,如何寫開頭和結尾,寫作素材就是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經歷。
范雨素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一天》,用時間表完整記述了她一天內做的事情。那時,14歲的大女兒已經出去打工,為了照顧二女兒,她在村子附近的一個幼兒園尋了個老師的工作,每個月2000多元。范雨素每天早上6點20分起床,洗漱后到幼兒園上班,給飲水機上水,幫學生盛飯,看他們吃飯,給生病的孩子喂藥,還要根據教材給孩子們上語言課,帶孩子們做游戲。孩子們午睡時她批改作業。下午4點20分學生放學后,她負責打掃教室的衛生。在這份安排得滿滿當當的日程表里,只有兩段時間是最愜意的——早上步行上班時聽古詩詞,晚上下班路上聽鋼琴曲。早上時間匆忙,范雨素走得快,20分鐘就能到學校,晚上卻慢悠悠地晃了一個小時。在這兩段時間里,她是自己最想成為的范雨素。后來,她還寫了一篇《農民大哥》,1000多字,講哥哥追尋文學夢不成,最后老老實實當農民的故事。這篇稿子發在一個非虛構寫作的公號上,讓她獲得了2000元的稿費。
范雨素說,與之前相比,皮村通往北京市區的公交車多了好幾輛。圖為皮村車站(夏天 攝)
?
在洗碗工、地攤小販、育兒嫂之外,北京的范雨素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寫作者。尤其在《我是范雨素》發表后,她成了文學小組里名氣最大的作者,被選為小組文集的主編,每兩個月寫一篇卷首語,千字左右。每篇卷首語她都寫得很認真,要想個十來天才能下筆。因為不想被人認出是育兒嫂范雨素,她不愿意再去需要登記個人信息的家政公司或者App搶活兒,只在一個小時工群里,偶爾接些私活兒,每小時只有30元。不做零工也不寫作的時候,她有時在家,大聲朗誦古詩或者自己寫的詩歌,讀到熱淚盈眶;有時出門,聽著音樂,去皮村隔壁的溫榆河走一走。只要天氣不熱,她都會戴上圍巾,薄的、厚的,紅的、紫的,她換著戴,“累計得有30條”。來北京后,她見到的文學寫作者們都喜歡這樣打扮。
科幻和穿越
文學小組的老師張慧瑜畢業于北大中文系,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教師。在范雨素出名前,他就聽她講過要寫一本小說,有關家人的前世今生。張慧瑜當時很吃驚,在給他留下印象的工人文學作品里,詩歌和散文比較突出,小說非常少。“寫小說不僅需要對文字精準的表達能力,還需要大量時間進行推敲。”而一般勞工階層的時間,大部分得用在維持生計上。
但范雨素下了決心。從2015年開始,她就在醞釀這部小說。一開始用的是穿越劇形式。沒寫多久,又覺得穿越形式這些年被寫得太多,太低端了。當時,劉慈欣的小說《三體》獲得第73屆世界科幻大會“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她覺得科幻更高級,有讀者,所以自己也去看物理學相關的書,包括加來道雄的《超越時空》、大栗博司的《超弦理論》,還讀了《給嬰兒的量子力學》。
“拾到籃子都是菜”,范雨素把零零散散自學的物理學內容都加進了小說。她并不擔心自己是否能夠駕馭這些理論,也不擔心讀者是否能讀懂她博采眾家、雜糅演繹后的理論。對于讀者和作者的關系,她有一種樸素的樂觀。她舉了一個例子,人大附中的教師李永樂在網上講科學,有8000萬粉絲(其實是543萬),“既然是粉絲,肯定能看懂他講的東西”。
往科幻轉型的作品,發生在一個更宏大的空間——楊六郎、楊門女將和楊過結為族人,影星范冰冰也成了她的族人,還有動畫片里的角色、兒童歌謠、流行歌曲的歌詞,前幾十年所有的閱讀和見聞,她都剪輯拼接在一起。主角仍然是自己的家人:母親、舅舅、父親……父親是前世的帝王,母親今生是來給他贖罪的,舅舅是“力拔山兮”的將軍,他們都通過喝孟婆湯穿越到現在,在湖北襄陽打伙村成為一家人。促成穿越的,除了命運的神秘力量,還有一些物理學的智慧,比如光的波粒二象性。原本這個概念是講光的特性,既能像波一樣向前傳播,又像其他粒子一樣具有能量。范雨素想,那項羽的力量就這樣通過光跨越時空,傳到舅舅身上吧。雖然現實里,舅舅只是村里一個普通農民,既不是大力士,也沒有練過武功。
她給自己設定的角色是一個無名氏,原型是“一飯千金”典故中的洗衣婦:大將韓信在未得志時境況困苦,常去河邊釣魚果腹。河邊有一個洗衣婦看他可憐,總是把自己的飯送給他吃。韓信說自己功成名就之后會報答她。洗衣婦聽了很不高興,說給飯并不是希望獲得對方的報答。但韓信功成之后,還是給她送了一千兩黃金。范雨素想以這個故事表明,自己雖然窮苦,但靈魂高貴,終得福報。
范雨素說,想通過這本科幻小說,將過去、現在、未來疊加在一起,表達如果突破時空的界限,“人和人之間并沒有階級差異,是自由和平等的”。小說里寫了一個戰國的大官,沒有出人頭地之前,所有親戚都對他愛搭不理,等他衣錦還鄉之時,親戚們又在五里地外跪著相迎。范雨素說,這個“大官”也是家人的前生,前世帝王身,今生不得志。如果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誰都會有窮有富,所以不用在意現在的苦難。
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文學小組的一位成員記得,有一天范雨素拎著三個大袋子走進小組辦公室,驕傲地將手稿攤在桌子上,像展示自己的稀罕家當一樣說:“這就是我的手稿,十幾斤重,大概有100多萬字,寫死人了。”后來,有人幫她將稿子輸入電腦,累計6.5萬字。
“那些不真實”
在我們采訪的那天,范雨素剛看了一則新聞,一個女人靠做育兒嫂四年,替丈夫還清了80萬元外債。“如果我沒有出名,老老實實賺錢,40萬元應該有吧?”說到這里,她停頓了一下,“2018年,我當時一個月工資有6000元,現在怎么也得七八千。”但因為投入這本書的寫作,她推掉了大部分其他可以賺快錢的活兒。找她約稿的人越來越少,上一次收到稿費還是一年多前。去年額外的收入是參加了一個公益組織的活動,開了兩次線上會,拿了1700多元的會務費。
她付出了現實的代價,卻還沒有找到欣賞這本書的人。從市場的角度看,出書和拍電影有相似之處,風格明確的類型片,更能滿足市場期待。而范雨素的作品,不屬于任何一類。非虛構?虛構?科幻?玄幻?很難分得清楚,她也拒絕做區分。因為和編輯無法達成一致的修改意見,小說的出版計劃停滯了。手稿放在張慧瑜那里,他在幫她尋找新的出版社。張慧瑜覺得,不能以嚴肅小說或者非虛構文體來要求范雨素現在的寫作。他以一位導師的善意提醒記者:“如果(把小說)看作是一種屬于她的特殊文體呢?”
可有多少作者有能力讓市場接受一種獨屬于自己的文體呢?即便她是范雨素。而且,她還只是范雨素——這是一個并不強壯的新生的名字。以往在村子里,大家都叫她的小名“紅菊”,在北京擺地攤時,別人叫她“湖北佬”,當了育兒嫂后,比她年紀大的雇主叫她“小范”,年紀小的叫她“范大姐”,或者直接叫她“阿姨”。
“你的真實經歷是你最寶貴的東西,也是大眾愿意看的。為什么不寫呢?”采訪那天,我問她——這也是我和其他跟她接觸過的編輯交談后共同的疑問。
“我不想寫,我覺得那些不真實。”范雨素又是搖頭。
對她來說,真實早就消失了。從12歲開始,她就和家鄉的親人,和過去的自己漸行漸遠。今天的范雨素落腳在一個距離家鄉1000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唯一的聯系是每隔十多天給母親打一次電話,敘敘家常。老家原來存著很多小時候的讀物,有一次家里漏雨,把書淋濕了,被家人曬干以后堆在廚房里,用來燒柴引火了。母親現在和哥哥住在一起,談起女兒,她用得最多的話是“折騰”,“端過盤子,當過保姆,她過得最苦。要是能待在家里,像她四姐一樣當個老師多好”。但范雨素并不覺得四姐過得好。因為小兒麻痹癥導致殘疾,四姐嫁給了一個農民。她雖然很少和四姐聊天,卻能從四姐的眼神和表情里讀出不快樂,有跟她一樣被家暴后的閃躲和害怕。小哥哥的生活更是一言難盡。因為賭博,不僅欠了一屁股債,還丟了工作。成名之后,范雨素偷偷給小哥哥塞了3萬塊錢,是她做育兒嫂時存下的。“我不欠別人錢都過得這么難,他欠了那么多錢,別人會怎么看他和對他?肯定過得更難。”
范雨素很少直白地談自己與家人的情感,但會舉出一個又一個例子給你聽,都是她從手機上看來的。她說起一則新聞:每月到了領低保的那天,銀行門口總有六七十歲的老人排隊。老人們不會操作機器,就請工作人員幫忙,工作人員問為什么不讓孩子代領,對方回答:“代領了兒女就不會給了。”這則看似與她無關的新聞,范雨素重復了好幾遍,“農村里的感情是涼薄的。母親雖然對我好,但她的每一滴汗水都要流到我的兩個哥哥碗里,她幫不了我什么”。
和范雨素的理想世界比起來,這些都是不真實的。故鄉的貧窮不真實,母親的不幸福不真實,自己經歷過的苦難不真實,像浮萍一樣,和親人的被迫疏離不真實。所有弱者的被輕視、被欺凌都不應該“真實”,她背井離鄉走了那么遠的路,就是想離開這種“不真實”。而真實,存在于一個更為浩瀚廣闊的時空,就像她努力,甚至有點吃力地試圖用文字建立的那個時空。在那里,她和家人歷盡百劫,跨越千年,仍然在一起。

金俊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