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strike id="c00c2"></strike>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1927年,我軍相繼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
三大起義,是我軍在革命最低潮時迎難逆行、厚積薄發的必然結果。起義軍的來源,除了追求進步的舊軍隊,后兩個起義還動員了農民和工人。
三大起義都處在敵強我弱、民智未開的大環境下,打不贏就跑、上山打游擊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但能做到這一點卻非常不容易。
事實上,三大起義失利以后,只有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而有7位元帥參與的南昌起義和3位元帥參加的廣州起義,不是在轉移中消耗就是選擇固守城池打陣地戰,這是為什么呢?
分析起來,三大起義的初衷相同但結局不同,主要有幾個原因。

原因之一:三大起義的出發點,都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產物。
發動武裝起義,為什么要借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
1924年,中山先生在蘇聯的幫助下創建“黃埔軍校”,又通過東征消滅了陳炯明叛軍。
中山先生病逝以后,1926年廣州當局、武漢當局接連發起兩次北伐,消滅了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又配合西北軍馮玉祥打跑了奉系軍閥張作霖,可以說戰果輝煌。
在莫斯科的指導下,中國的革命者也參與其中,并對俄國的紅色革命有了深刻認知。
1927年,蔣氏在上海發起“四一二”事變,武漢有爆發了“馬日”事變,隨后“寧漢合流”,沆瀣一氣殺戮革命者。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危急時刻,我黨決定借鑒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經驗,在有條件的大城市發動武裝起義。
當然,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城市中心論”。

原因之二:三大起義的最終目標,都是“奪取中心城市”。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有幾點:一是實現工農聯盟,二是武裝暴動,三是通過中心城市發動起義,因為“十月革命”就發生在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
在我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都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束縛,試圖攻打長沙、武漢、南京等大城市。而陳獨秀、向忠發、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城市中心論”的忠實踐行者。
所以,三大起義的目標是一致的:奪取中心城市,進而把革命推向全國。而三大起義選擇的目標城市,分別是江西第一大城市南昌、湖南第一大城市長沙,以及廣東第一大城市廣州。
但是,由于敵眾我寡實力懸殊,南昌起義成功后敵軍四面包抄,劉伯承的參謀團只好擬定了南下潮汕方案;
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雖然打下瀏陽縣城,但難以守住,更不要說攻打長沙了;廣州起義明知敵軍四面圍城,仍然固守,結果三天時間守軍幾乎傷亡殆盡,余部撤離廣州。
而三大起義的連續失利,說明在中國“城市中心論”是站不住腳的。

原因之三:三大起義發起時,還沒有走出舊式軍隊的思維模式。
三大起義,是我軍獨立創建武裝力量的第一步,但步履艱難。
由于第一次大合作有過三年多的“蜜月期”,我軍內部同時跨兩個組織的名將,不在少數。
此外,在國民革命軍中還誕生了我軍第一支武裝力量:大總統府鐵甲車隊,也就是后來的“葉挺獨立團”,但陳獨秀等一直反對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這也是大革命失敗的一大教訓。
三大起義,是我黨深刻認知“槍桿子”的第一步。
但是,三大起義依賴的主力軍,還是來自舊軍隊的進步力量。其中,南昌起義的主力,是葉挺11軍24師、聶榮臻動員的25師,以及周公爭取的賀龍20軍,共2萬余人,幾乎清一色來自舊軍隊。
秋收起義是“八七會議”后,上級派主席去發動的。5000余人的起義軍主力,是盧德銘的第二方面軍武漢警衛團,以及安源、萍鄉、瀏陽、平江等地農民自衛軍,此外還有修水土匪邱國軒所部。
廣州起義的主力軍,是葉劍英的第二方面軍第4軍教導團、警衛團一部2000余人,以及周文雍領導的工人赤衛隊3000余人(徐向前任6大隊大隊長),此外,海、陸豐農民赤衛隊也舉行了起義。
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雖然有工人赤衛隊、農民自衛軍參與,但都是偏師。

原因之四:從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到廣州起義,有一個發展過程。
三大起義發起時,我軍對“槍桿子”的認識一步步深化:南昌起義時,我軍對部隊番號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認知,打著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旗號,同時還寄希望張發奎舉行起義。
但是,南昌起義的失利說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寄希望舊軍閥是不現實的。
到了秋收起義時,主席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秋收起義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旗號,師長由舊軍人余灑度擔任,但余灑度中途叛逃再次證明,沒有理想的舊軍人是靠不住的。
廣州起義比前兩次起義更進一步,建立了蘇維埃,主席是張太雷。
原因之五:對三大起義的指揮權,莫斯科的控制程度不同。
1924年到1927年,蘇聯的影響很大,像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總顧問加侖將軍,就是后來的元帥布柳赫爾,葉挺獨立團的蘇聯顧問是后來的元帥崔可夫,還有一個就是鮑羅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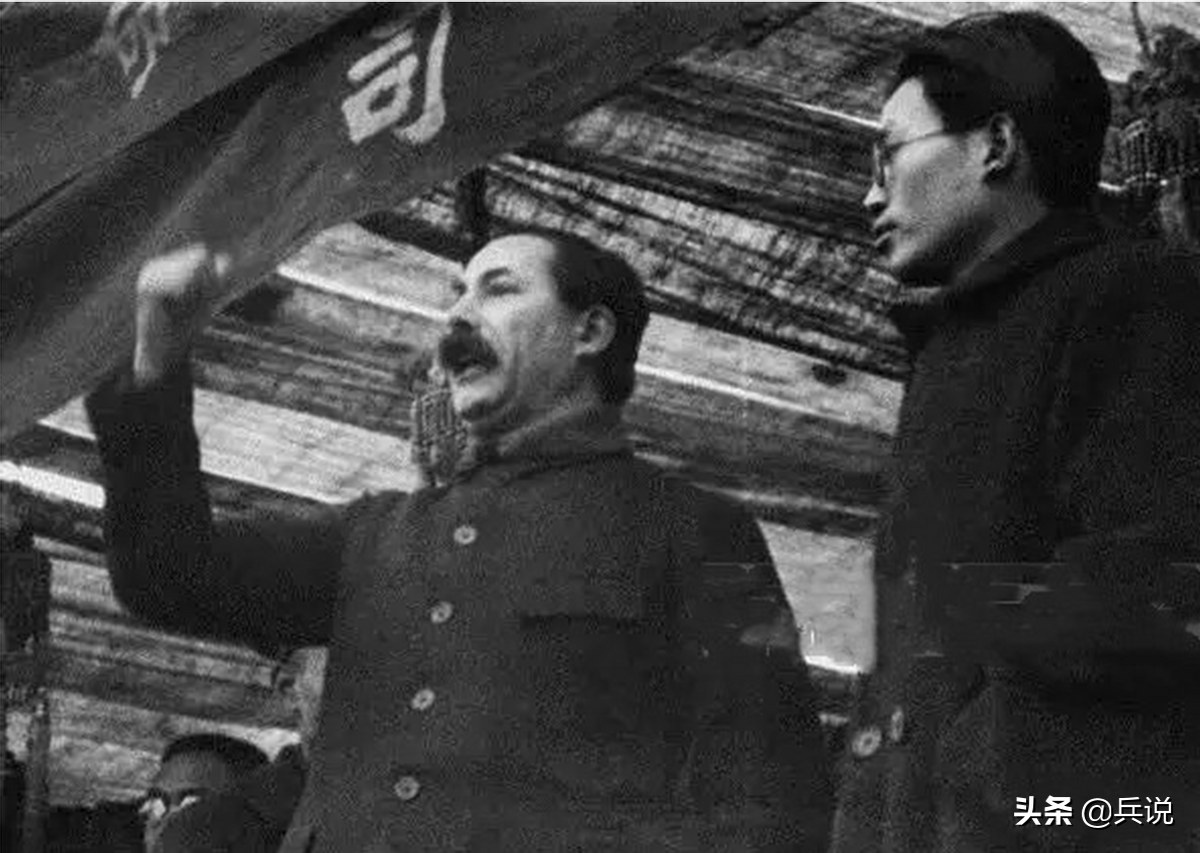
1927年7月,鮑羅廷建議陳獨秀和譚平山去莫斯科開會。
此舉實際上變相解除了陳獨秀的領導權,張氏、李維漢、周公、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五常委”。南昌起義前,張氏以莫斯科的名義推遲起義,遭到周公、李立三、譚平山等大多數人的反對。
秋收起義,是主席領導的一次武裝起義,受莫斯科的影響最小。
廣州起義,不但得到莫斯科30萬美元的資助,還受到莫斯科代表諾伊曼的直接插手干預,起義三人組是張太雷、黃平和周文雍,但總指揮是葉挺,副總指揮是葉劍英,參謀長是徐光英。
諾伊曼否決了葉挺、葉劍英撤離廣州的正確建議,一味死守導致損失慘重。

原因之六:三大起義失利后,只有主席首先想到了“上山”。
廣州起義失敗后,高層有的人把責任強加在總指揮葉挺頭上。很顯然,這是不公正也是不客觀的。后來江西蘇區“洋顧問”李德瞎指揮更離譜,直接加速了紅軍喪失了根據地。
沒有“洋顧問”插手的南昌起義,為什么就沒想到“上山”呢?
南昌起義誕生了十大元帥中的七位、十大將中的三位:
總指揮賀龍,前敵總指揮葉挺,公安局長、第9軍軍長朱老總,參謀團團長劉伯承,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第4軍參謀長葉劍英,團黨代表陳毅,營長陳賡,連長林總、許光達,班長粟裕。
這么多科班出身的名將,都沒人想到“上山”。南昌起義部隊經歷了三河壩分兵、潮汕失利、湘南起義后,才在朱老總、王爾琢和陳毅帶領下,上井岡山和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

由此可見,主席掌舵方向的偉大!
我軍一旦上了山,就如同猛虎添翼:井岡山會師,開辟了新紀元;江西蘇區依托羅霄山,打退敵軍四次“圍殲”;舉世矚目的萬里長征,把萬水千山踩在腳下;寶塔山下,主席等人指揮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前奏。
而開國將帥在主席的指揮下,一旦下山就勢不可擋:八路軍下了太行山、沂蒙山,又走進長白山和大別山;最終,以工農為主的解放大軍,將紅旗插上了十萬大山、天山和喜馬拉雅山!

馬書
<ul id="ugus2"></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