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碎片時間已經成為我們當下最為熟悉的概念。當我們在排隊等待或者通勤時,拿出手機已經成為一種普遍行為。如同電視改變了人們對客廳的看法一樣,移動設備也占據了我們日常生活的閑暇時間。對此,一些人認為,這種“私有化的移動”猶如一道屏障,把公共生活拒之于外;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移動設備會凸顯并激勵人們在公共空間中的既有行為和應對策略,提供了額外的靈活性,或者自在、熟悉的感覺。
佐治亞州立大學教授伊桑·圖西認為,這些閑暇時間創造了一種碎片時間經濟,商家可以通過創造產品、應用程序、平臺、訂閱服務、微支付和互動的機會,利用大眾的注意力來盈利。隨著商家將我們的閑暇時間商品化,移動設備成為促銷、品宣和分銷的重要工具,消費者也將移動設備作為瀏覽公共和私人空間的一種手段。移動設備在利用我們的碎片時間為商家創收的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控制感和連接感。這些設備不僅改變了我們使用和規劃時間的方式,還改變了我們與他人互動的方式,改變了我們對空間關系的看法。
在《閑暇變現:如何搶占海量碎片時間》一書中,伊桑·圖西通過探索碎片時間經濟的四個主要場景:工作場所、通勤途中、等候室內和“互聯”的客廳,闡明了娛樂產業和數字賦能公眾之間的關系。
他闡述了這些具體的場景:在工作場所,碎片時間經濟為努力工作的格子間上班族提供了“傳媒零食”,這些職場人希望通過最喜歡的跨媒體制作,了解即將到來的比賽、更新的劇集或上映的電影。在通勤路上,訂閱服務幫助移動用戶制造了一個“傳媒泡沫”,讓人們能在上下班途中短暫地放松。在等候室,休閑類游戲嘗試利用人們的煩躁,他們會不時查看自己的移動設備,希望從中獲得價值,借此記錄自己在休息時間取得的成就。在客廳,第二屏應用程序和推特 Amplify 嘗試預測電視觀眾的需求,把移動設備當作看電視時不可或缺的良伴。
以下內容節選自《閑暇變現:如何搶占海量碎片時間》,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丨[美]伊桑·圖西
摘編丨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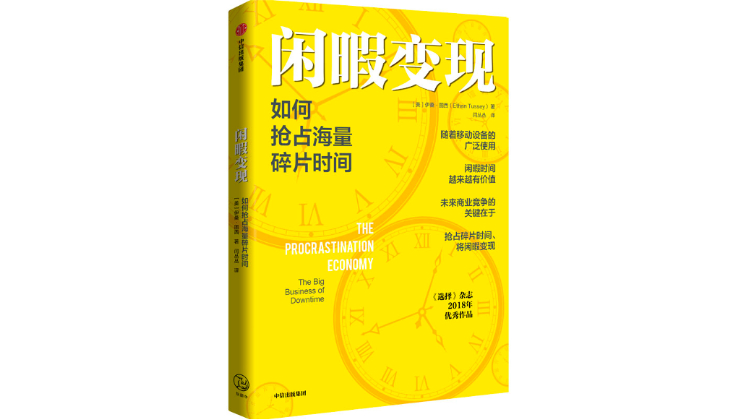
《閑暇變現:如何搶占海量碎片時間》,[美]伊桑·圖西(Ethan Tussey) 著,閆叢叢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4月版
移動技術是如何一步步延伸到社交和文化活動中的?
喜劇演員路易斯·C.K.(Louis C.K.)經常毫不留情地諷刺移動手機及其用戶,在表達個人對移動技術的擔憂時,他指出,這一技術會讓人不斷分心,看不到生活的真相:“正因為有手機,人們才會邊開車邊發短信。我環顧四周,發現所有人在開車時都會發短信。這無異于謀殺,每一個這樣做的人都在拿車里乘客的性命開玩笑。但是人們甘愿冒著生命危險,甘愿這樣自我毀滅,因為他們連一秒的孤獨都不能忍受,孤獨的感覺太難受了。”
路易斯的反諷反映出他對傳媒技術的擔憂,這是學者們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的話題。傳媒和傳播技術改變了人與外界的關系,模糊了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的邊界。在評估電視技術的可供性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了“移動的私有化”這一概念,形容電視讓人們足不出戶卻可以對外界了如指掌。在分析移動電視時,琳恩·斯皮格爾把威廉斯的這個詞顛倒了一下,變成了“私有化的移動”,用該詞來描述移動設備讓人們能夠在公共場合感受到像在家一般自在。人們每一次使用移動設備獲取其在移動媒介上的私藏,或在公共場合進行私人對話時,都是在享受這種私有化的移動。移動設備的批評者視之為一層隔離罩,讓里面的人與外界隔絕。
移動設備常常猶如一道屏障,把公共生活拒之于外,因此人們總認為移動技術不利于培養同理心,不利于大眾團結。文化理論家喬納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認為移動設備導致愈演愈烈的個人主義,人們可以用設備來改變其在公共場合的個人體驗。邁克爾·布爾認為,移動設備可以制造一個“有聲泡沫”,讓市民同胞之間彼此隔離。大量圍繞移動設備的研究都把關注點放在移動設備對社交的影響上。茲茲·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在其著作中寫道,移動設備提供了一方私密的小天地,讓人在公共空間中依舊能感到自在。

電影《社交網絡》(2010)劇照。
對帕帕查理斯來說,在公共場所使用移動設備是一種政治行為,人們通過“維系現有的關系,并建立新的關系”,從而維護了其個人自主性。斯科特·坎貝爾(Scott Campbell)的研究證實了帕帕查理斯的某些論斷,他發現移動設備通過進一步鞏固本就牢固的關系,抵制脆弱的關系,形成了一種“關系網私有主義”。從本質上說就是,這些設備讓我們與所愛之人更容易保持聯系,同時也幫助我們與身邊的人或事撇清干系。
移動設備會凸顯并激勵人們在公共空間中的既有行為和應對策略。如果我們要聚焦碎片時間經濟,應將移動設備置于合適的空間場合和歷史背景下。其實,人們早就開始使用傳媒技術來填充碎片時間了,現代移動設備不過是這歷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只有理解了這一歷史,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碎片時間經濟和其背后的邏輯:支持移動設備的使用,認可努力利用移動用戶的習慣創收。學者們在探究移動設備的技術可供性以及設備為何受歡迎時,往往忽視了背景因素。
比如,坎貝爾主張,移動設備,尤其是智能手機,其可供性提供了“額外一重靈活性,在傳播信息、通信和內容的同時,又不影響用戶繼續從事其常規或非常規的事務與活動”。坎貝爾對技術的評估很準確——移動設備確實滿足了隨時與外界保持溝通的需求——但這一技術可供性并不決定用途,也不曾反映為什么人們會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移動設備。坎貝爾的“關系網私有主義”說明我們使用自己的移動設備是為了尋求自在、熟悉的感覺,但碎片時間經濟的歷史表明,我們其實一直都在借助媒介實現這一訴求。如能從特定場域的媒介這一歷史背景出發考慮移動設備,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認識到移動技術是如何一步步延伸到社交和文化活動中的。
人們會在社交場合使用移動傳媒來改善周圍環境
個人移動設備的流行讓我們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但是,相比休閑和娛樂消遣,我們在“消磨時間”、多任務并舉或碎片時間中所從事的活動經常被看作小事一樁,不值一提。文化批評家和學界認為電影、電視以及視頻游戲均是值得分析的藝術形式,而拖延、浪費碎片時間則是效率專家主攻的方向,是需要克服的壞習慣。
盡管蒙受這樣的污名,但整個歷史進程中的移動傳媒使用情況揭示出了,不同的技術如何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穿插娛樂、遠距離通信以及藝術等。碎片時間經濟的歷史表明,移動技術一直用于提高生產效率、娛樂消遣和社交等,以適應特定的社交和空間關系。
同時營銷公司和傳媒公司瞄準了碎片時間經濟,試圖利用種種移動習慣盈利。碎片時間經濟的歷史是一部人們在公共場合不斷使用移動技術來宣告個人支配權的歷史,而傳媒公司支持這種渴望,特別優待那些經常把碎片時間花在移動傳媒上的人。
傳媒傳播學者杰勒德·戈金(Gerard Goggin)指出,媒體對于手機使用的報道讓人們重新開始擔憂公共和私人空間界限的崩塌。拉里莎·約爾特(Larissa Hjorth)和英格麗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指出,原來家庭內的、私人的和個性化的東西通過手機—— 一個親密的“指尖上的家”——成了相當流動的、微媒化的東西,同時將“身臨其境”的體驗轉變為了“如臨其境”。手機在很多方面擴展了斯皮格爾提出的“私有化的移動”的理念,提供了一種只需待在手機所創造的私人移動空間中,就能輕松與世界對話的方式。

電影《竊聽風云2》劇照
移動傳媒的歷史解釋了一種由來已久的情況,人們會在社交場合使用移動傳媒來改善周圍環境,彰顯自我。移動設備提供了獲取娛樂、信息和進行交流的渠道,可以改變公共領域的物理和社交屬性。文化理論家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認為,隨著工作和休閑之間的界限崩塌,人們開始想辦法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采取應對措施。碎片時間經濟下的公司和機構為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動設備規定了有傾向性的行為和社交秩序,傳媒公司的生財之道和移動用戶的創意之舉輪番登場,圍繞控制權和意義尋求展開拉鋸戰,兩者共同定義了現代生活。
社交媒體平臺也是碎片時間經濟的一部分
移動設備給消費者帶來了種種便利,使之能隨時進行社交,對物理空間擁有了更多掌控權,與此同時,傳媒公司利用這些移動設備從碎片時間中盈利。娛樂公司努力用自己的內容和服務讓消費者忘掉無聊乏味。有業界衡量指標,比如“參與度”和“收視率”來評估哪些產品和服務最能讓消費者投入時間和精力。廣播行業(電視和收音機)為各種公司瞄準移動受眾做了示范,因為它們率先踐行了“時段”(比如,清晨、白天、黃金時段、深夜)策略,每天不同時段的體裁、審美和形式都在迎合相應的受眾需求。
受根據時段安排節目的啟發,尼克·布朗(Nick Browne)這樣的學者開始分析節目安排表,認為這一點證明了電視行業所用的方法就是,構建一個理想的觀眾群,用圍繞日常的意識形態之爭來吸引觀眾。比如說,肥皂劇題材就是專為下午安排的,制片人瞄準的就是在家的媽媽們,所講述的故事可以穿插在家務之外的碎片時間中。布朗認為分時段的節目安排表把電視變成了一種文化體制,因為通過節目單可以看出,廣播電視網能夠反映和強化“工作日、工作周的社交媒體秩序”,并能“在工作和休閑兩個世界中找到平衡”。這些節目安排的策略把電視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一個時段的設計都是為了深化工作和休閑之間的鴻溝,碎片時間經濟圍繞我們的碎片時間打造了移動版的時段。
碎片時間經濟的內容和規劃通過把那些在等待、拖延和消磨時間的人塑造成行為主體,同樣也調和了效率和娛樂之間的緊張態勢。傳媒公司創作內容、應用和服務,所基于的觀點就是我們會轉向手機來填充碎片時間。電視和電影發行商,電纜服務提供商以及流媒體平臺通過在移動應用上傳播、重新包裝或拓展其故事世界,推動了碎片時間經濟。
社交媒體平臺也是碎片時間經濟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提供“群組文娛”(communitainment),這是斯圖爾特·坎寧(Stuart Cunningham) 和戴維·克雷格(David Craig)所創的術語,指娛樂行業基于用戶的創意和社交媒體平臺上的交流來創造媒體內容,努力參與數字社群的活動。移動設備生產商和視頻游戲開發商通過開發供特定場合使用的移動功能,推動碎片時間經濟發展。盡管公司經常發布的某一項移動策略,其實只是努力把這種休閑經濟應用于移動設備,但努力為特定場合的移動設備使用定制內容和服務,對碎片時間經濟也同樣適用。本書詳細介紹了傳媒公司如何調整其移動策略,關注特定的場合和受眾。正如電視學者會分析時段以了解其潛在的意識形態,碎片時間經濟反映了行業對移動受眾的看法。
那些推動了移動時段的公司同時也推動了對碎片時間經濟背景下的理想受眾的定義。從移動設備的設計功能、內容和服務中可以看出其追捧的目標受眾。碎片時間經濟青睞的受眾與艾琳·米漢(Eileen Meehan)對電視收視率的研究中描述的“商品受眾”有很多共同之處。在這篇論文中,米漢分析了電視收視率的歷史沿革,解釋了宏觀經濟架構如何影響節目安排的決策和對受眾的認識。宏觀經濟分析表明,電視行業的“評估形式是基于經濟目標選定的,而非依照社會科學的原則”。
跟收視率一樣,傳媒行業努力想要理解移動受眾,也是源于其渴望利用碎片時間實現經濟創收。比如,伊麗莎白·埃文斯(Elizabeth Evans)指出,那些移動視頻游戲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免費增值的商業模式,利用的正是游戲玩家的煩躁。免費增值的游戲面向所有人,誰都可以免費玩兒(有些是帶廣告的),但對那些有可支配收入的玩家來說,他們享有直接跳過游戲內規定的等待時間的特權。
理解碎片時間經濟背后的宏觀經濟現實十分重要,因為移動設備已經成了互聯網的主要渠道。碎片時間經濟的發展與互聯網的商業轉型不謀而合。傳媒學者喬納森·齊特(Jonathan Zittrain)認為,隨著傳媒行業建立數字商業模型,互聯網初期特有的“繁殖”精神正逐步消失。在《連線》(Wired)2010 年8 月刊中,編輯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和作家邁克爾·沃爾夫(Michael Wolff)提出,萬維網終于邁入商業發展階段了。他們解釋說,隨著移動計算的興起,“利用網絡進行傳播,而非僅僅借瀏覽器來展示的半封閉平臺”掌握了特權,簡化了網絡導航,創造了方便的傳遞系統。這種更方便、更有商業發展前景的互聯網的興起,讓互聯網使用過程中的某些常態趨于標準化,賦予了碎片時間經濟特權。
2007年,iPhone(蘋果手機)的發布是碎片時間經濟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它引入的移動設備可以執行多項任務,能夠為忙碌的消費者分憂。在iPhone 發布前夕,蘋果公司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將iPhone 標榜為“重新定義用戶可以用手機做什么”的設備,結合了三種產品:“一部手機,一臺寬屏iPod(蘋果數字多媒體播放器),以及互聯網。”蘋果一開始的營銷計劃主攻iPhone可以完成的多種任務,但從2007 年起的第二波廣告則開始重點關注來自iPhone 用戶的溢美之詞。

電影《社交網絡》(2010)劇照。
尤其跟碎片時間經濟相關的是一則專題廣告,主人公名叫埃利奧特,廣告講述了他的故事,一次埃利奧特去參加晚宴,努力想要記住老板未婚妻的名字。在這則廣告中,埃利奧特說,在等老板來的空當中,他用自己的iPhone上網搜索老板未婚妻的名字。另外幾則廣告,分別把鏡頭對準了企業家、湊在一起打賭的人、臉書用戶,以及一個遇上天氣延誤的飛行員等,他們紛紛把手機作為在日常生活中從容打發碎片時間的工具。
智能手機和聯網移動設備模糊了工作和休閑之間的界限
智能手機的功能也影響了互聯網公司和社交媒體平臺,兩者紛紛開始優化自己的網站,方便移動端使用。自智能手機開始盛行,臉書一直是移動客戶青睞的終端,它從2006年起就開發了一個移動平臺,也是在同一年,在平臺開始研發沒多久,臉書就引入了自己的新聞流,重新設計了網站的功能,新聞流相當于一個個性化的“新聞聚合器,可以在用戶的社交網絡上發布具體的活動,突出與人相關的信息、用戶參與的活動,以及用戶選擇分享的其他信息”。新聞流曾被稱為“社交網絡史上最重要的一項發明”,對碎片時間經濟而言,這一評價十分精準,因為它成了移動設備專為社交而添加的標準設計。
在新聞流之前,臉書用戶需要主動搜索朋友們更新的狀態,而重新設計之后,所有更新的狀態都會自動刷新內容流。這樣就從兩個層面上推動了碎片時間經濟。第一,有效改變了社交網站的商業模式,從網頁瀏覽變為廣告贊助的社交互動。第二,簡化了臉書的導航,從而使平臺成為可靠的移動應用,可以利用白天的碎片時間與朋友保持聯絡。廣告商現在可以瞄準這些碎片時間,清楚在哪種場合自己投放的廣告比較吸引人。盡管重新設計一開始引發了眾怒,但它并未影響用戶對臉書的熱情,畢竟它一直都是用戶最多的移動應用之一。此外,界面設計和廣告商業模式也成為定義和獲得移動受眾的標準策略。

電影《竊聽風云2》劇照。
在互聯網平臺優化其網站以方便移動端使用的同時,電影公司、電視網以及品牌經理開始把智能手機看作推廣產品和服務的新屏幕。比如,2007 年,華納兄弟娛樂公司創造了一個特別的子公司——華納兄弟家庭娛樂,負責數字傳播。華納兄弟家庭娛樂的任務包括封裝式記錄媒體光盤和藍光光盤、電子銷售影片服務點播和下載文件,以及設計數字平臺和工具(游戲和社交媒體推廣)以支持其媒體資源。2011年,這一子公司收購了社交電影網站Flixster,后者擁有電影評論網站爛番茄(Rotten Tomatoes)。
華納兄弟的數字團隊利用Flixster 的品牌和影評數據庫,設計了一個移動應用。用戶可以通過此應用獲取其平臺上收集內容的電子副本,包括電影評論、影片在網飛上的排名,以及為移動消費者提供電影票和電影信息的各種搜索工具。在查克·特賴恩(Chuck Tryon)看來,這一應用在嘗試為消費者提供“平臺移動性”(platform mobility),換言之,讓消費者可以從任何設備上獲取各媒介所收集的內容。無論是通過Flixster 這款應用,還是華納兄弟在臉書、75iTunes(蘋果播放應用程序)或是比特流(BitTorrent)上的嘗試,公司與數字受眾之間一直培養的關系類似一種承諾,即受眾將能在路上看電影和看電視。重視通過移動端獲取內容,源于努力想把家庭娛樂的策略用到移動受眾身上。
盡管在數字傳播方面的投入經常忽略具體的使用場合,傳媒公司還是制作了很多平行文本和短視頻,比如宣傳視頻剪輯、品牌定制客戶端、表情包鍵盤以及GIF生成器等,都能助推碎片時間經濟的發展。無論其初衷如何,人們確實會在其碎片時間使用這些產品和服務。
碎片時間經濟在智能手機和聯網移動設備盛行的時代迎來榮發展,是因為這些技術模糊了工作和休閑之間的界限,特賴恩的“平臺移動性”的理念和琳恩·斯皮格爾與馬克斯·道森(MaxDawson)的“靈活休閑”(flexible leisure)道出了行業在努力將移動傳媒定位成可以隨便吃的自助餐,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盡情享用。但與之相對的是,碎片時間經濟詳細地體現了娛樂業如何努力吸引移動受眾在不同的場合借“零食化”的內容和社交媒體對話來填充自己的碎片時間。接著這一比喻往下說,碎片時間經濟的產品和服務就猶如快餐食品行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斯皮格爾和道森認為,這種全新的全年24小時無休的后工業時代信息經濟“后天心律不齊”,將促使電視網放棄習以為常的時段,和基于8小時工作日的受眾戰略定位。盡管工作日已經發生了變化,對消費者注意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娛樂公司還是希望定義移動觀眾所處的場合,雖然斯皮格爾和道森把“靈活休閑”看作點播內容背后的商業邏輯,但仔細研究媒體行業的努力方向則可以看出,分時段安排節目這種做法并未就此消亡,碎片時間經濟背景下到處都是特意設計的內容和服務,對準工作場所的、等候室的、在通勤途中的,以及在“互聯”的客廳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群相應的“傳媒零食”習慣。點播服務讓消費者有了一定的支配權,他們可以決定在何時如何利用內容,但是傳媒公司還是可以決定選擇的內容和其可及性。因此,移動設備歸根結底還是由碎片時間經濟背后的思維方式定義的。
作者丨[美]伊桑·圖西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進
導語校對丨陳荻雁
來源:新京報網

王陽
